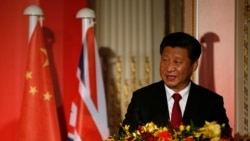20年4月,瑞典的最後一所孔子學堂也在南部小城法爾肯貝里關閉,瑞典成為了歐洲第一個與孔子學院徹底告的國家。沒有了孔子學院,瑞典的中文教育並沒有停頓。
瑞典是歐洲第一個引入孔子學院的國家。05年2月,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開辦了歐洲的第一所孔子學院,這也是世界上第一所開課的孔子學院。然而十年後的15年,斯德哥爾摩大學結束了與孔子學院長達十年的合作,理由是“在大學系統中存在由其他國家資助的機構,這是令人質疑的做法”。
在剝離了中國政府的直接影響後,瑞典的漢語教育依然還保持著穩定,很多瑞典的年輕人仍然對漢語和中國文化抱有興趣。
孔子學院,這個依照歌德學院、塞萬提斯學院和法語聯盟建立的漢語語言和文化推廣機構,其形象正在轉變為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輸出“中繼站”,並每每出現在表達對華強硬立場的語境裡。
比如英國的前財務大臣里希·蘇納克(Rishi Sunak)在7月底的電視辯論中,為了展示其在中國問題上展示強硬立場,承諾倘若當選,將關閉在英國的30所孔子學院。
而德國聯邦教育部長卡利切克(Anja Karliczek)也在去年10月發表過類似的擔憂,她對德國的19所孔子學院的活動“深感憂慮”,並認為,孔子學院對德國高校工作的影響已經變得顯而易見,這是“不能被接受的”。她建議有關高校“認真審視和孔子學院的合作”,“果斷地處理”中國的影響。
20歲的朱莉亞-馬歇(Lulia Marcher)是烏普薩拉大學的一名大一新生,她將在9月開始為期兩年的漢語進階學習課程,並且打算在這期間到中國交換留學一到兩年。
朱莉亞來自瑞典中部的厄勒布魯,這里之前沒有開設過孔子學院或孔子學堂,但她所在的高中有漢語母語的老師和會說漢語的瑞典老師,她說她更喜歡那位會說漢語的瑞典老師,因為他會和學生一起討論一些問題。她從高一開始學習漢語,這也讓她開始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並成為這她想在大學進一步深造漢語的原因。
在孔子學院離開瑞典的兩年後,瑞典的各級漢語教育系統並未發生太大變化。其中,2020年在大學裡學習漢語的人數甚至有所增加。
當然,這和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有著一定的關聯。“疫情對瑞典國內的就業市場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因此很多人選擇到大學上學,這從客觀上也推動了大學漢語學習人數的增加。但總體上,在大學學習漢語的學生人數還是比較穩定的”,瑞典哥德堡大學語言與文學系的高級講師和系副主任楊富雷( Fredrik Fällman )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
楊富雷是一名研究中國宗教的漢學家,在瑞典的大學系統裡已教授了二十多年的漢語。其中,在2005年和06年,他還參與了斯德哥爾摩大學孔子學院的創建,以及初期的教學和管理的工作。
他表示,從漢語教學的角度看,孔子學院的離開肯定是造成了一定的損失。因為,孔子學院的中國合作方復旦大學派駐到斯德哥爾摩大學的老師,不僅有著很好的教學水平,而且都擁有和語言學專業相關的博士學位。
“在瑞典的漢學界現在很少有人在做語言學研究的了,因為時代不同了。所以,這些有語言學博士研究背景的老師是很難得的”,楊富雷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漢學研究在瑞典的大學裡本身就是一個很小眾,很少得到關注的領域,所以,能夠得到那麼多高水平的師資力量,對漢學在瑞典的發展本身來說是件好事”。
海外的漢語教育一般分為兩個部分,針對非漢語母語者的漢語教育,和針對有漢語母語家庭背景的漢語教育。孔子學院的漢語教學對像多是前者。而孔子學院也分為兩種類型,與當地大學合作的,以成人為對象的“孔子學院”,以及與當地初、高中合作,以在校初高中生為對象的“孔子學堂”。
孔子學院徹底離開瑞典,從整體上看並沒有對瑞典的漢語教育體系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比如,最先選擇退出和孔子學院合作的斯德哥爾摩大學,其本身就擁有很長的漢學研究傳統,固定的行政編制以及良好的漢語教學師資。所以,選擇退出並不會對其漢語教學和學術研究產生負面的影響。
但是,其他幾所與孔子學院合作的大學的情況就有些不同了。比如,2012年成立孔子學院的呂勒歐工業大學,這所在成立之初被稱為“世界上最北,緯度最高”的孔子學院在2019年關閉。和斯德哥爾摩大學相比,呂勒歐工業大學的漢學學術傳統和漢語教學師資顯然是無法相提並論的。因此,孔子學院的離開,對於當地的漢語教育無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即便是教育資源相對豐富的地區,也存在著同樣的情況。
翟怡嘉現在居住在瑞典中部的烏普薩拉,她曾是當地孔子學堂的一名漢語老師。在國內大學主修俄語的她,在畢業不久後就來到瑞典開啟了對外漢語教學的工作,在16年到19年的三年間,在當地的一所高中和兩所初中教授漢語。
烏普薩拉當地的烏普薩拉大學,是瑞典規模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大學,大學裡也開設有漢語專業。但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翟怡嘉表示,“孔子學堂關閉後,當地的初高中這幾年就沒有開設漢語課程了,因為沒有老師去教了”。
早在2006年,瑞典政府就做出了讓漢語成為瑞典初高中選修課的決定,並製定了教學大綱。但瑞典政府在之後並沒有積極地支持這一政策的落地,比如從財政上支持瑞典的大學系統培養漢語教育的師資力量。這也使得瑞典的很多地方自治體在缺乏足夠的財政和師資的情況下,不敢貿然在初高中開設漢語課程。
“只有斯德哥爾摩的幾所初高中開設了漢語課程。而像哥德堡,只有一所高中開設了漢語課程。瑞典有幾個城市的初高中漢語教學做得很不錯,但這主要是依靠教師自身的努力去做的”,楊富雷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楊富雷同時也強調,選擇不和孔子學院繼續合作,並不是因為瑞典政府的要求,這是每所大學自己做出的決定。“瑞典政府和孔子學院的關閉之間,是沒有任何關係的。有些國外媒體說,瑞典政府關閉了最後的孔子學院什麼的,但瑞典政府沒有做出這樣的決定。但瑞典政府和教育部肯定會討論這個問題,但是他們不會影響到大學自己的決定。雖然大學是國立大學,但是是獨立的,決定權在大學本身,不在政府。”
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成立孔子學院的初期,就有來自大學內部的質疑聲,主要是集中在,大學系統中是否應該讓一個由其他國家資助的機構存在。並且由於中國政府的國際形象的轉變,讓這種質疑變得更加合理。
“從05年到15年的這十年間,中國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發生了一些變化,越來越成為一個'自傲的強國'。中國國內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關於公民社會,宗教自由,民族權利等等,這些之前是睜隻眼閉隻眼的問題,現在成了兩隻眼睛都睜得很大,什麼都要管理,什麼都要壓制”,楊富雷這樣說道。
這也是孔子學院自身存在的一個硬傷,無法提供一個與西方社會相匹配的自由言論空間。因為自我閹割了關於宗教和民族權利等所謂“敏感”話題的討論,只限定在傳統文化和語言教育的提供者,是無法滿足現代自由民主社會對於教育機構的需求的。
楊富雷在採訪中也表示,“比如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孔子學院裡,有學生想要討論這些所謂的敏感話題,那除了孔子學院的老師外,他還可以找到其他的了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瑞典老師來討論。但是在像呂勒歐這樣的地方,除了孔子學院外,可能找不到其他了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地方”。
法國半官方智庫,國家軍事學校戰略研究所(IRSEM)在2021年曾公佈了一份名為《中國影響力行動》的報告,梳理了中國政府近年來為擴展影響力而部署的日趨深入而且廣泛的全球網絡。在關於孔子學院的部分。
該報告顯示,該機構會獲得來自大使館的支持和協調,並接受國家漢辦的管理。當一所大學同意合作成立孔子學院時,將會獲得不同數額的財政援助來啟動該活動,每所孔子學院每年平均會獲得10至15萬美元的撥款。孔子學院的教師均由漢辦招聘和培訓,而教學資源(書籍、音頻或視頻)也是由漢辦來製定的。
無疑,與中國的合作和交流,這些政治風險就一直存在。楊富雷表示,“我們做漢學家的都知道,黨的影響到處都有,出國的人員裡也有黨員。我們的責任是要培養瑞典的媒體,多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如何更好地和中國接觸”。
至少在孔子學院的問題上,瑞典的教育機構們在衡量了潛在的風險後,選擇了保持距離。雖然孔子學院提供了免費且質優的師資人員,但孔子學院接受的是來自大使館和國家漢辦的管理,並且更為重要的是,提供這個免費資源的國家還是個日趨專制的政權。
瑞典的漢語教育市場在今年也出現了一張新面孔,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這個由台灣政府資助的語言教育機構從去年開始,已經陸續在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出現。
但孔子學院的經歷似乎讓楊富雷產生了強大的免疫機能。他說在5、6年前,他就接到過一個來自名為“台灣學院”的機構的邀約,“我們(指大學方面)都覺得要保持距離,因為這也是一個政府機構。雖然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但作為一個瑞典的國立大學,不管合作的機構在什麼地方,我們都需要保持管理的自由和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