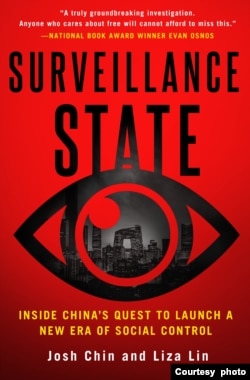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治下,中國是如何在過去十年裡成為一個監控國家(Surveillance State)的?習近平和中共為什麼要這麼做?監控國家給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帶來哪些影響?美國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應該如何應對?華爾街日報兩名資深記者——該報中國分社副社長李肇華(Josh Chin)和駐中國記者林和(Liza Lin)最新出版的新書《監控國家:中國尋求開啟社會控制新時代的內幕》(Surveillance State: Inside China's Quest to Launch New Era of Social Control)試圖解答這些問題。
兩位作者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中共領導人把過去的極權統治手段與高科技相融合,重塑對整個中國社會的控制。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新疆,但其目的並不是要消滅一個宗教少數群體,而是要通過高科技將其重塑。兩位作者說,中國作為一個數字監控的大國,正在迫使全球各地的民主國家在有關信息、安全和個人自由之間關係的問題上與中國交鋒。
李肇華說,撰寫這本書的初衷要追溯到2016年和2017年間。當時,他們觀察到中國社會發生的一個重大轉變,就是中國共產黨正激進地重新回歸到管理普通百姓生活的做法,這與中共自19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退出對人民微觀管理的做法相違背。
李肇華回憶起2017年他前往新疆採訪報導的經歷。那次經歷讓他領教到在中共無所遁形的監控網絡下那種令人窒息的感覺。“特別是在2017年和2018年,當時正處於鎮壓的高潮,那種監控的程度令人窒息,監控無處不在。”
李肇華表示,中共希望通過高科技手段來補足威權體制的短板,那就是應變問題的能力。“共產黨一直在尋找方法來提高反應能力,他們相信現在有了人工智能的這些最新科技,有了關於社會如何運作的大數據,他們可以建立一個系統,不僅像民主國家一樣反應迅速,而且可以更迅速應變,因為它可以預測未來的問題。”
林和說,中國的監控系統通常都是政府與企業合作的產物,通過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方式實現,由一家大型企業比如華為、海康威視和大華作為主要投標方競標政府項目,這些大企業然後會尋找一些較小的企業進行合作,比如商湯(SenseTime)、依圖科技(Yitu)和曠視科技(Megvii)等。
“政府與企業形成一種共生關係,”她說,“這些AI企業通過與政府合作讓他們的算法,比如人臉識別的算法越來越成熟,因為它的改進需要大量的數據,通過與中國政府的合作,這些公司能夠獲得大量的人臉數據。這些數據僅靠他們自己是無法獲得的,如果靠自己的話就需要很長的時間。”
林和表示,自2020年開始的新冠疫情將中國政府對公民的全面監控推向了巔峰。
她說:“新冠疫情確實為中國開創了一個監控的新時代,因為在過去,你通常不會被24小時實時監控,除非你是一個被中國公安部定義的七類人之一……新冠疫情擴大了中國國家監控的範圍,超出了之前特定人群的範圍,擴大到了全民監控。”
以下是本次專訪的主要內容節選。
記者:請你們首先介紹一下寫這本書的初衷?
李肇華:寫這本書的最初想法要追溯到2016和2017年。在那個時候,我們開始注意到中共政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當時共產黨非常積極地把自己重新註入到中國民眾的生活當中。這與幾十年來中共從管理人民生活擺脫出來的做法是背道而馳。中共現在要告訴人們該如何生活,並且想要了解人們在做什麼。我們探究瞭如何報導這個故事的方法。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但我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2017年年初,林和當時的工作是追踪中國的科技初創企業。她發現巨額的投資資金流入中國科技行業的一個領域,那就是AI(人工智能),特別是電腦視覺和人臉識別。於是她給我打電話,說在北京有一家非常有意思的公司,叫商湯(SenseTime)。我們就去看了一下,走進他們的展廳,就像走進了一部科幻電影,牆上有一個大屏幕,上面是一個街道的實時視頻圖像,畫面上出現的任何東西都被自動打上標記,比如,從行人到汽車、自行車等等。我們意識到這項技術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強大。後來我們發現,他們向中國警方出售了大量的技術。所以,這就是我們寫的第一個報導,是關於人臉識別的。然後我們做了一個系列的報導,最後是我做的一個關於在新疆的報導。我在2017年去了那裡,那是在我們真正了解到那裡底發生了什麼之前。我們當時只是聽到了一些傳言,說那裡使用了大量的監控技術。我後來去到那裡,那是一段令人震驚的經歷,就像是到了一個反烏托邦的戰區。他們對一個少數民族使用了大量的尖端技術,使用這些技術把他們送到集中營。當我們看到這一切時,我們意識到我們手上有了一個大題目,而我們需要用一本書的篇幅來充分探討其中的問題。
記者:能否講一講您在新疆採訪報導的經歷?
李肇華:我仍然記得我在新疆所感受到的身體上的恐懼,特別是在2017年和2018年,當時正處於鎮壓的高潮,那種監控的程度令人窒息,監控無處不在。你有這樣的感覺,比如,就是無論去哪或者是做任何事情都被追踪。而我還只是一個去那裡訪問的外國人,當地維吾爾人的感受就可以想像了。我在新疆時,我們和一個維吾爾人交談過。雖然他沒有被寫進書裡,但我認為他的經歷非常典型。他是一個住在烏魯木齊的人,以前曾與警察發生過衝突,發生過一些小摩擦,結果他被列入黑名單。這個人基本上寸步難行,他不能離開他的小區,因為每次他想出去時,他都要通過一個安全檢查站,掃描他的身份證和他的臉,然後警報就會響起。警察不讓他出去。長期下去,他就有點被逼瘋了。他基本上是生活在一個監獄裡,一個露天的監獄。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就好像是20世紀才會有的東西又重現了,比如配備了高科技的集中營或者是針對宗教少數群體的拘留營。我們以前從未見過的。那是一段非常、非常令人震驚的經歷。
記者: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在構建“監控國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林和:在我們的調查中,我們發現中國安裝的很多安全系統,其實就是監控系統,通常是政府與企業合作的產物,通過公私合作的方式(PPP),往往有一家規模很大的公司,比如華為、海康威視、大華或者是中國電信作為主要的投標方,競標政府合同和政府項目,他們使用名為“系統整合”的方法,有一家主要的投標方,然後再把項目分給一些較小的公司。通常你會看到像商湯這樣的公司提供AI,監控AI。在這些項目中,較小的公司要和大型企業合作,比如海康威視來提供監控攝像頭。中國企業與中國政府之間肯定存在著一種共生的關係。比如,像商湯這樣的企業,還有它的競爭對手依圖和曠視,這些AI企業通過與政府合作讓他們的算法,比如人臉識別的算法越來越成熟,因為它的改進需要大量的數據,通過與中國政府的合作,這些公司能夠獲得大量的人臉數據。這些數據僅靠他們自己是無法獲得的,如果靠自己的話就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中國企業與政府之間肯定存在著一種互惠的關係。
記者:中國的監控與西方美國等民主國家有何不同?
李肇華:國家監控不是新鮮事。事實上,它歷史悠久,從國家誕生之初就已經存在,古羅馬人通過收集人口普查數據來弄清如何向人們徵稅,一直到東德的斯塔西(前東德國家安全部),再到911之後的美國《愛國者法案》。各類政府都參與並依賴國家監控來運作。我認為中國的不同之處在其規模和野心。在規模上,中國有4億個監控攝像頭,其中很多攝像頭都具有人臉識別能力,它們可以跟踪個人,可以在人群中識別人。中國有10億部智能手機,中國政府可以相對容易地獲得這些手機的數據。它可以跟踪他們去過哪裡,以及他們如何使用手機的,這只是對人類行為的大規模了解,我不認為任何其他政權或政府或國家在歷史上曾經擁有過這麼多數據。中國政府的野心,他們想用這些數據幹什麼,也遠遠超出了我們所看到的任何東西。他們相信,他們可以利用這些數據並對其進行分析,從而使他們能夠建立一個完美設計的自我糾錯的社會。如果你研究20世紀的歷史,這些曾經都是他們熟悉的烏托邦願景,但在20世紀,它們只是夢想。而現在在中國,中共認為它們可以使其成為現實。如果你比較一下,比如說你把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和美國比較一下。在美國,當然也有很多監控,這些工具中的一些也被美國警察使用。但不同的是,(美國)顯然有法律的製約,有法治,在美國有自由的媒體,可以監測所有這些東西,也會有很多媒體報導,這要歸功於報紙和其他媒體對這些(監控行為)的報導,以及(監控)手段在美國被使用的方式。但在中國,中共不受這些限制。
林和:中國和西方之間最顯著的區別之一是權力集中在一個實體內。因此,如果你比較美國的數據收集量,我們並不是說它比中國少。但是,如果你看一下美國在收集什麼樣的數據,誰在收集這些數據,亞馬遜、谷歌、Facebook等公司,他們也有大量的消費者數據。顯然,像聯邦調查局這樣的國家安全機構。他們也有大量的數據。但在中國,情況是你能得到的所有數據都集中在共產黨內部,儘管黨、國家、法院、公安系統之間有細微的界限。因此,從技術上講,中國政府和中共可以獲得所有這些數據,這與西方和美國的情況不同,因為在美國,數據被分佈在不同的實體中,而不是只掌握在一個實體手中。
記者:中共的國家監控體系如何改變中國社會?
李肇華:我認為,如果回顧一下西方與中國交往的早期,比如在中國試圖加入世貿組織時,人們普遍認為西方或者高科技能夠使中國民主化。但顯然,現在發生的事情正好相反。中國正在使用高科技來加強對權力的控制,並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強對權力的控制,我認為你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特別看到了這一點。在疫情期間,他們動用了政治意願和直接的野蠻封控措施,用監控技術對人們進行管控,不只是控制疫情,壓制病毒傳播,他們已經相當成功,而且還用監控技術壓制公眾對疫情封控的憤怒和反抗。中國各地都有人對他們受到的嚴厲封控措施感到非常憤怒。但中共一直能夠阻止這種憤怒髮展成更大的群體事件,所以這確實是一個中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高科技來實施控制的情況。
林和:新冠疫情確實為中國開創了一個監控的新時代,因為在過去,你通常不會被24小時實時監控,除非你是一個被關注的人,也就是中國公安部定義的會被關注的七類人之一,即上訪者、可能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的人、潛在恐怖分子、精神病患者等,凡是屬於這七類人的,警方通常會實時監控。我認為,新冠疫情后,實時監控從只監控特定人群變成監控全民,因為現在每個人的手機裡都有一個健康碼,無論你走到哪裡都必須出示這個健康碼,它能追踪到你在過去兩週內都去過哪裡。而且如果你在一個城市裡停留了4個小時或更長時間,那麼它就會被記錄在你的健康碼中。因此,政府現在在任何時候都能知道每個人在哪裡,並將這些信息收集。因此,新冠疫情擴大了中國國家監控的範圍,超出了之前特定人群的範圍,擴大到了全民監控。
記者:美國為什麼要關注中共對中國公民的監控?美國能夠做些什麼?
李肇華:我認為,如果你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你相信民主價值觀,我想你會明白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應該對你很重要,因為中國正在積極嘗試給這些(監控)技術定義其使用規範。中共在推廣這樣一種願景,即政府使用這些技術進行政治控製或以他們想要的任何方式使用這些技術是沒問題的。你可以從他們出口這類技術的方式中看到這一點,他們在全球範圍內推廣這種技術。儘管他們還沒有一個具體的計劃,他們沒有說其他國家政府需要如何復制中國的模式,但他們的確表示,各國政府應該能夠使用這些技術來施加控制,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願景。而民主國家現在對這個問題沒有解答方案。因此,我認為這是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們在看待未來的全球政治時真正應該考慮的一件事。中國已經提出了一個願景,而民主世界的回答將是什麼?
林和:我認為美國已經邁出了第一步,試圖限制中國取得可能被應用到中國監控系統的美國技術。例如,限制可能出售給中國人工智能初創公司的高端技術,這些公司可能將其用於深度學習,從而提升攝像頭的監控能力。我認為,下一步的好辦法也許是通過多邊方式來確保這些部件不會落入中國監控公司的手中,這些公司會延續他們在新疆使用這種系統的方式更多地使用這種系統。因為現在,即使美國有像貿易黑名單和投資黑名單,甚至有法律禁止一些非常重要和關鍵的美國組件進入中國的監控公司,仍然有大量的漏洞。因此,為了填補這些漏洞,而且很多時候,這些漏洞涉及從不同國家轉運。我認為,美國採取多邊方法並與盟國合作,以確保你能真正切斷中國監控國家的一些重要組成部分,這將是一件好事。
記者: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李肇華:國家監控對習近平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助推。他在過去10年中如此努力地實施它是有原因的,表現在幾個不同的方面。其中一個方面是,他是一個非常雄心勃勃的領導人,他在中國實施了很多改變。他因此樹了很多敵人,他對中國有一個願景,實現這個願景會涉及很多痛苦和許多重大的破壞性變革,如果他能夠成功的話,特別是在他進入第三個任期的時候,有一個允許他在落實這些變革時施加更多控制的系統,這是至關重要的。在某些方面,如果他對自己控制社會的能力沒有信心,他甚至不可能設想實施這些措施。我認為,國家監控對他的另一個幫助是,這不僅是習近平的問題,也是幾個世紀以來中國領導人都面臨的問題,那就是,中國一直是一個難以治理的地方,因為它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一直有一個非常龐大的官僚機構,信息往往不能很好地流向首都,流向北京。在我們這個時代,習近平是一個我認為真正需要或想要獲得信息的人。他想知道各地發生了什麼。至少在理論上,監控國家允許他看到各地發生的事情,我認為,其最終效果仍有待我們的觀察。在中國的官僚機構中,肯定有人不希望他看到全部,他們在破壞監控國家。我認為,我們還要看習是否確實積累了足夠的權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美國之音進行一系列採訪,反映有關美國政策的負責任的討論和觀點。被採訪人所發表的評論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