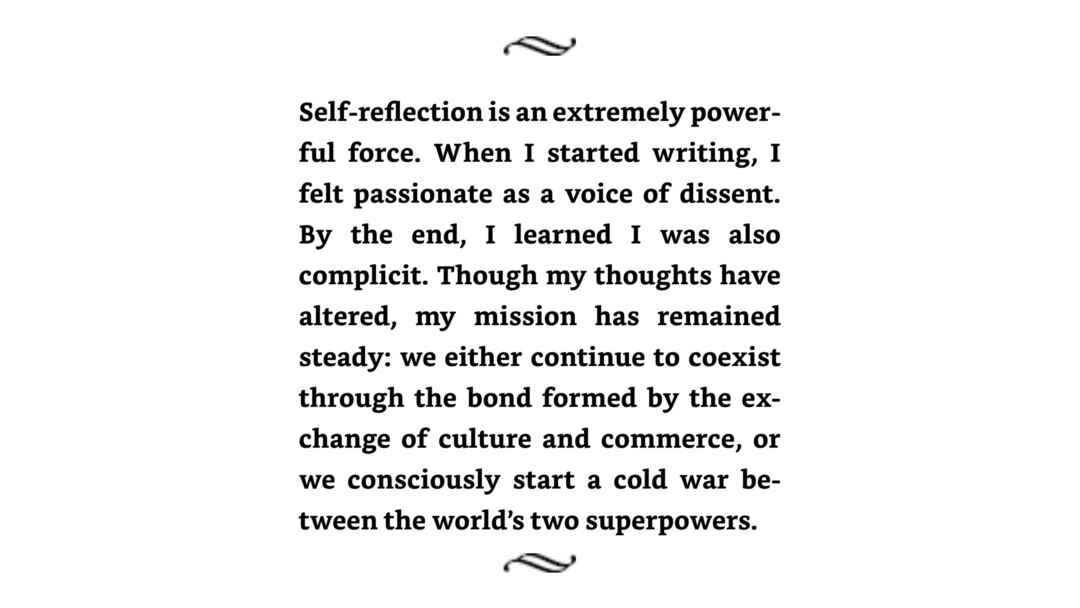
芬頓在回憶錄的扉頁上關於“自省”的感悟。(截屏)
《投餵中國龍,置身於好萊塢、NBA和美企面臨的萬億美元難題》( Feeding the Dragon: Inside the Trillion Dollar Dilemma Facing Hollywood, the NBA, & American Business ),這本批評荷里活為市場而逢迎中國政府的警世之作,2020年8月出版後,引發巨大反響。作者芬頓也作為“曾經的餵龍人”而被定格在美中關係的宏大舞台上。
時隔數月,“餵龍人”芬頓和他的這部回憶錄(以下簡稱《投餵中國龍》)近來再度被熱炒。美國之音記者因此專訪了芬頓,請他分享更多“投餵中國龍”的應景啟示。
Your browser doesn’t support HTML5
“餵龍人”芬頓:為甚麼直到特朗普上台才拉響警鐘?我們需要反思
記者:芬頓先生,很榮幸您能再度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我們看到,法國廣播電臺本月初專訪了您,並做了長篇報導。這受到媒體廣泛注意,包括一些中國以外的中文媒體也敏銳反應,再度熱議您這位曾經的“餵龍人”和您的《投餵中國龍》。您的回憶錄出版數月後,為什麼再度被熱炒?
芬頓:我也很高興你們再次採訪我。我是美國之音的粉絲,認為你們的使命符合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利益。事實上,我與美國之音中文部和英文部都有著不淺的淵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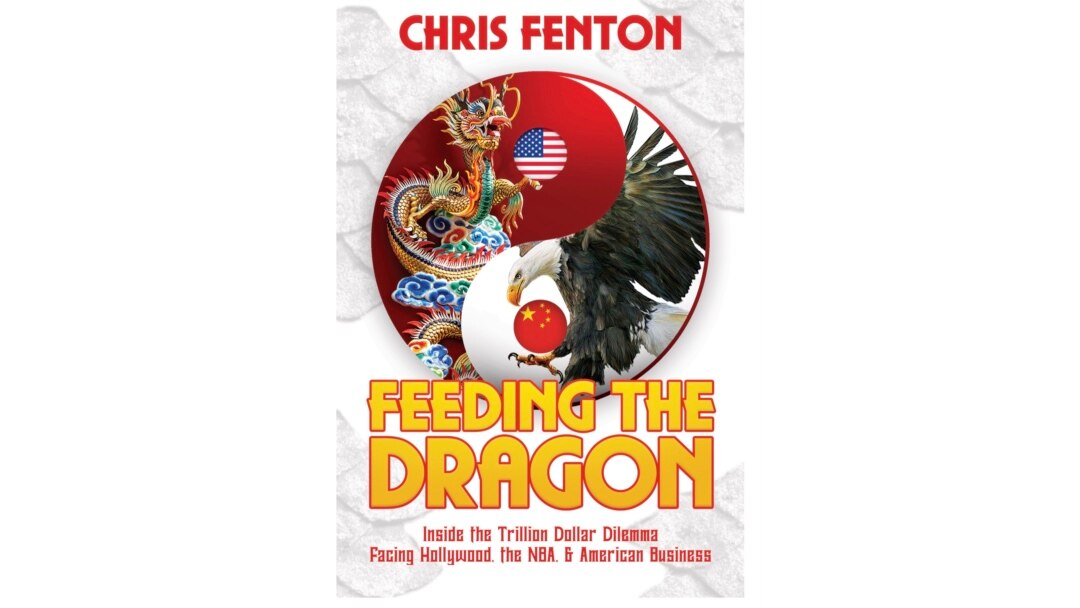
荷里活製片人克里斯·芬頓所著回憶錄《投餵中國龍》一書的封面。(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的那本《投餵中國龍》出版之後,甚至之前,都受到廣泛關注。此前,因為美國選舉全面鋪開,特朗普的共和黨頻繁談論中國對美國的挑戰,而荷里活、NBA都是很高調的行業,我們自然成為討論美中關係的一個部分。而我的那本書正好在這樣的形勢下,就像在一堵牆上打開了一個洞,讓原來牆後的一切變得一目了然。
選舉結束之後,美國國內政治一度成為焦點,人們更關注政權的和平移交。這一切完成之後,如何應對中國重回視線,包括特朗普政府制定的政策是應該延續下去,還是將壽終正寢;還有拜登在中國問題上會讓怎樣的一些顧問和官員圍繞身邊,比方說國務卿,國家安全機構負責的人選等。所有這些都圍繞拜登是否繼續強硬對待中國。
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仍然嚴重,顯而易見,我們的中心思想是疫情來自中國,本來是中國的問題,然後變成了我們的問題。而且,我們看到,中國的態度依然好鬥和具挑釁性(aggressive),包括南中國海的軍演,通過政府手段禁演一些電影,比方說《無依之地》,對該片導演趙婷發動的言論攻勢,還有特斯拉因為批評南昌電網而道歉,後被新華網批“傲慢”等等,這些現像都獲得媒體關注。這也說明,這段時期,中國挑戰沒有變化,而且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更加清楚地看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它們或許感到,《投餵中國龍》裡的故事的確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重播。
記者:我想美國等西方國家徬徨的應該是未來如何與中國共存,是黑臉唱到底,還是保留某種程度的紅臉。您如何認為呢?
芬頓:我要說的是,我不是鴿派。如果完全的鴿派是1分,完全鷹派是10分的話,我大約是6分,偏向鷹派。但是,我不想跟中國打熱仗,也不希望打冷戰,而是認為我們兩個超級大國需要想辦法共存。
我認為,我們頂多是戰略競爭對手,同時也心知肚明,兩國不會做朋友。我說的是兩國政府,而不是兩國人民。從人民的層面來說,我很喜歡中國,也有很多中國朋友。
文化和商業交流是我們經常談到的五個支柱中可以共同合作的兩個。我們需要改變過去的交往方式,為兩國製造公平,這是美國及其盟友更需要重點對待的。
我不認為政治、國安和人權方面我們和中國會有一致看法,至少不會在可見的未來達成一致。讓我們把這些放在一邊,把重點放在文化和商業交流上,找到一個公平的方式。
我認為,進入美國人為中國創造的資本市場是中國走到今天的根源,就是金融市場培養了中國對我們的競爭能力。此外,在每個企業,包括好萊塢在內,我們願意轉讓技術,辦合資企業,教中國人如何學習我們的做事方法,同時卻沒有保護我們自己的知識智慧產權,而且這些都是明明知道在給自己製造對手的情況下做的。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在1800年代早期也上演過類似的劇本,只不過當時的美國也是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一些不好的做法是企業個體行為,而不是政府行為。我們當時要追上歐洲工業革命,偷竊了歐洲很多技術之類的。有一天,歐洲說,嘿,美國,夠了吧,請適可而止。這就是我們需要告知中國的時刻。可是,為什麼一直沒有這麼做?為什麼等到高調的特朗普上台後才拉響警報?我們需要反思。
我們的確應該更早對中國說,請適可而止。比方說,美國證交所( SEC )應該說,要進入我們的市場,你們要遵循與我們同樣的會計標準,就像任何美國公司一樣;世貿組織也應該把中國歸類為發達國家,總之,我們需要在方方面面的細節上製造公平的競爭場所。
記者:您現在認為,《投餵中國龍》在幫助美國從中國“解套”上可以起到什麼作用呢?
芬頓:我不想讓我的書太說教,太政策化,而是更想讓讀者看到,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如何捲入和陷得(entangled and stuck)這麼深;以及我們有多少優勢力量(leverage)來應對中國對美國的影響力,包括他們的經濟對我們那些想進入他們市場的企業和行業所造成的壓力。
我想到的是,如果能夠讓人們進入我說的故事中,看看我是如何捲進去的,以及如何在很多年以後才意識到這個問題。我還是很內疚,沒有看到當時自己做的事情長遠來說是有害的,直到2019年,我看到香港反修例運動如何讓美國NBA在中國遭遇禁播,才醒過來。我要讀者了解,多數人都在做我做過的事情,這才導致了今天的問題。
我們就像一台機器裡的一個齒輪一樣,專注於自己的領域,就是文化和商業交流,沒有要有意出賣美國的靈魂和我們堅守的價值和利益,儘管我們是資本主義,需要賺錢;誰都沒有為了進入市場而刻意出賣自己,當然也許有個別的會這麼做。多數人都在全球化的使命中,在竭盡全力打開市場,因為這也利於美國和世界盟友。
這是當時推動我的,但是時間一長,發現結果是助長了另一個大國的不公平競爭心態。這點不但我們個人需要反思,政府也需要反思。
記者:剛才您提到最近蜚聲影壇的年輕華裔女導演趙婷,因言論而受到中國批評,其金球獎獲獎影片《無依之地》在中國被悄悄取消上演的事情。有網友評論說,未來,荷里活不會再敢啟用中國人拍電影了,或者不讓他們涉足中國題材,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會踩到地雷陣。您認為是這樣嗎?
芬頓:我恰恰認為,荷里活應該回到拍攝好片子的時代,拍出好的電影和電視內容,不要再想著中國,只管拍好電影,讓電影業做好電影業。只要我們幹得好,自然有中國消費者來消費。現在還有一點,還有人問我,我們能否製作一些對中國來說的敏感話題?我的回答是,當然,我們應該這麼做,應該開始更多朝這方面走。不僅如此,我們還應該支持所有製片廠作為一個行業來行動,而不是單打獨鬥,以防止在中國遭到報復。只有進行行業聯合,我們才有力量對付報復。
對於中國來說,如果我們共同堅守,中國用後退來保住顏面是更加容易的選擇,因為政府可以用防火牆來阻擋不喜歡的內容進入。但是,荷里活可以把電影拿到世界其他地方去放映。我們還是可以贏。
我認為,現在整個荷里活都看清了中共,沒有誰不了解與中國政府打交道中所犯的錯誤,而且也認為,這些錯誤都應該糾正。儘管兩年前,我還莫名奇怪地傻到沒有意識到。
但是,也要看到現實的問題。不像亞馬遜這類與中國沒有歷史交往的公司,傳統的荷里活製片廠與中國打交道是有歷史的。而且,傳統荷里活的基礎設施現在受到高科技日新月異、新冠疫情和消費者味口改變的圍攻,所以,中國繼續成為製片廠與投資人、股東等談論的話題。我認為,傳統製片廠非常不情願討論事實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就是說,荷里活仍然在試圖盡很大努力讓中國對我們的活動感到激動,包括那些不對的事情。還有,荷里活也在失去市場,因為用我們這一套訓練了中國電影業,他們可以用自己的人馬拍出跟我們同樣水平的片子。更有甚者,他們在監管制度下變得更加強大和威風。
我認為,現在,荷里活製片廠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但是,又不敢公開承認,因為那會讓股東和投資人不安與擔心,也會導致對製片廠的評估發生改變。就是說,如果這些製片廠對中國表明立場,只能加速市場份額的丟失。
記者:我注意到您的播客用“投餵中國龍”命名,而且使用的口號是“芬頓與萊恩(另一名主持人)詳解中國最新新聞”。您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學術研究人員,卻致力於專門開節目來密集討論中國,您是否感到自己肩負著某種使命?
芬頓:我有兩個孩子,是金豬龍鳳胎,現在14歲。我的使命和目的就是,我堅定地相信,美中兩個超級大國某種程度上需要共享這個世界,這樣才能讓我活下來,讓我的孩子們活下來,也讓我的孫子們活下來。
我希望自己能做點什麼來推動兩國之間走向有建設性的方向。但是,我不是專家,雖然無數次來往中國,但是從來沒有在那裡住下過;雖然了解很多,但也知道我還不了解很多。
不過,我可以通過自己的方式,爭取呼籲每個美國人,告訴大家我們都與中國相關。我希望以此來獲得關注,來推動政策,不僅僅是政府層面的政策,也包括大公司層面的政策。
我認為,了解和參與的人多,就意味著我要講故事,要通過娛樂的方式,才能讓人懂;用日常生活的方式來吸引他們,這是我的作用。
我可以做到讓事情簡單化,要人們意識到,與另一個超級大國打仗或者進入冷戰,對我們來說都不是最有好處的。但同時,我們需要想出一個突破過去40年的方法,這是關鍵所在。
美國幫助中國建立了市場。我們要用符合美國堅守和引以為豪的價值觀,把錢賺回來,並讓中國也獲利,但是明白他們可能永遠不是我們的朋友,而且坦率說,可能永遠也實現不了民主;也許我們之間永遠也不可能建立榮辱與共的紐帶,但是,卻有必要矯正比賽場上的不公,讓兩國都獲得新的機會。
只有足夠多的人了解問題,這一切才可能發生。這就是我試圖在播客中做的。
記者:您回憶錄的名字“餵龍” ( Feeding the Dragon )已經進入到您的推名--“餵龍人” (TheDragonFeeder),以及您的播客名—同樣是“餵龍”。看來,這兩個字已經成為您的標籤,或者說您已經創立了一個品牌。這是您有意推動的,還是自然的水到渠成?
芬頓:人們也問我為什麼推文號是“餵龍人”,我的回答是,我必須與這個標籤共存,直到能夠推動出變化為止,就是不再餵龍為止。
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共謀,一切發展到今天,我也餵了龍,但是,我想改變這一切,哪怕只能起到一些微小的作用也在所不惜。事實上,這個品牌也在變得流行起來。
我在書裡披露,那個過程中的確有人提醒過我,說我在餵龍;我老婆也一再問我,說真要這麼餵野獸嗎,可能餵到一定程度後,野獸會變得失控,我說其實這就是中國,也許是一頭紅龍。她說,啊,就是餵食紅龍。這是一個有趣的插曲。我這個“餵食紅龍” 的主題是自然演化的。
讓我欣慰的是,這個名字每天都在給我動力,從背後推動我前行。當然,現在我們推動改變跟中國的關係,推動讓賽場變得平衡,肯定會引起一陣混亂。但是,當我們走出混亂之後,即便中國不會是我們的盟友,而是戰略對手,我們雙方的關係卻會變得更加健康一些。對我來說,這意味著一個更好的世界。
做到這點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我會一直戰鬥下去,抗爭下去。總要試一試,對吧。我很高興你為美國之音進行這樣的報導,因為你們擁有的是國際讀者和觀眾,而“餵龍”是一個全球性問題,正好契合。
現在,我們看到澳大利亞,英國和加拿大都在行動了。我認為,美國真需要盡快加入,以展示西方國家的團結戰線。
記者:感謝芬頓先生抽空接受美國之音專訪,並為解鎖美中關係提供思路。希望芬頓先生的子子孫孫都能平安幸福地在地球村里生活下去。
後記:根據娛樂業周刊《綜藝》( Variety )的報導,芬頓曾經擔任DMG娛樂公司的總裁,以及該公司的北美總經理。他是二十一部電影的製片人或者監製,這些影片在全球票房收入為20億美元。


